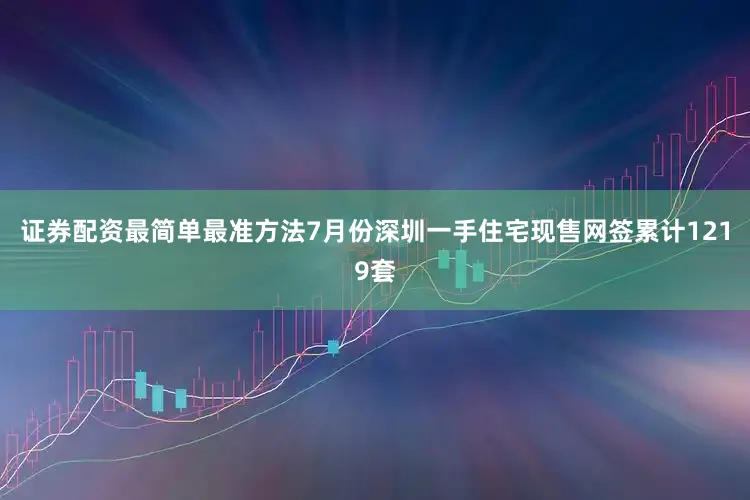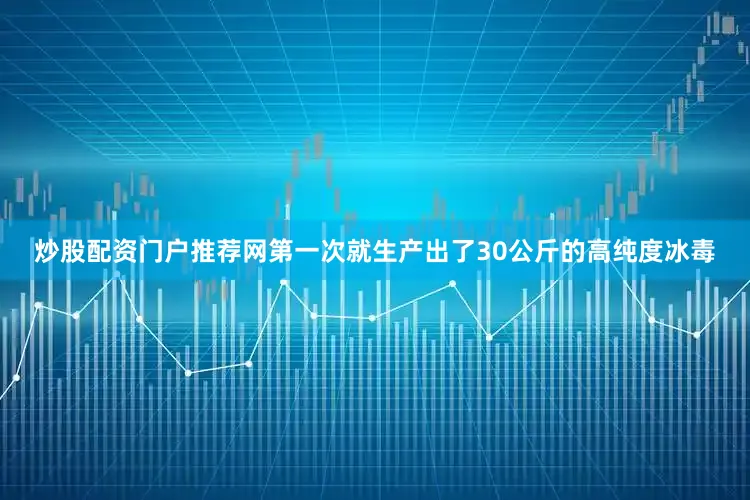2025年1月,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程方毅整理研究的《遥望与亲历:一个西方家庭眼中的中国(1887—1950)》一书出版,引发学界与公众热议。5月18日,以该书核心史料为基础的同名特展在中山大学博物馆开幕,数十张原版历史照片、首次公开的日记手稿、书信原件等“时间切片”,将一个近代美国医疗传教士家庭在华工作生活长达63年的真实经历全景呈现,该家庭作为近代中国变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其成员在华活动跨越医疗、政治、教育、外交等多个领域,为研究近代中外交流史提供了独特的微观史视角。展期至12月31日。
《遥望与亲历:一个西方家庭眼中的中国(1887—1950)》,程方毅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版
展开剩余88%展览以盈亨利家庭在华轨迹为线索,串联起晚清至民国的重大历史节点。第一单元“医脉相承”聚焦盈亨利家庭的起点——1887年秋天,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的盈亨利(James Henry Ingram)受到美国方面派遣,和妻子梅塔一起来到了中国北方通州。他担任了通州潞河医院首任院长,也深度参与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筹建。其大女儿盈露德(Ruth Ingram)追随父辈足迹,投身护理事业,作为中国现代护理学科奠基者,曾任协和护理学院第二任院长,1945—1950年间,她更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特派专员身份重返中国,曾在重庆、甘肃、晋察冀解放区等地提供医疗护理援助,还曾赴广州康乐村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考察交流。
盈亨利一家人在1912年左右的合影。前排右二为盈亨利,右一为伊萨贝尔;后排右一为盈露德。
第二单元“禁宫内外”堪称展览“重头戏”。伊萨贝尔是盈亨利的三女儿。她在中国出生、成长,后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1922年她从美国返回后,接替二姐米莉安担任“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习。本单元通过其1922年—1924年间撰写的日记、拍摄的宫廷影像及与家族成员的通信,聚焦紫禁城的黄昏时刻,展现一位西方知识女性对东方帝制的观察。伊萨贝尔既是文明碰撞的亲历者,也是时代剧变的记录者。她的日记中,还不乏对晚清“时尚达人”婉容穿搭的日常夸夸。从她以女性视角出发对服饰的敏锐感知,我们可以一窥20世纪初中国服饰文化经历的深刻嬗变。
盈亨利一家热爱旅行与记录,第三单元“中国见闻”通过他们留下的家庭相册、旅行手札、私人信件等,展现他们在中国的居住日常与跨文化体会——从北平的茶会与沙龙,到云冈石窟考察、承德与内蒙古的跋涉。这些碎片拼贴出一个西方家族在动荡时代中构建起的中西交融生活史,以及广袤的近代中国图景。从留存的照片可以看到,盈亨利一家不但与许多来华外国人有往来,也跟满族宗室毓朗、载涛,文化人士徐志摩、林徽因等人往来密切。
如果说伊萨贝尔见证了中华帝制的终结,那么她的姐姐盈露德则亲历了新中国的诞生。据策展人程方毅介绍,展览在三个单元之外另设了主题板块“探访解放区”,聚焦的是1947年底,盈露德与斯坦福大学临床外科退休教授利奥·埃洛瑟(Leo Eloesser)博士自天津启程,突破国民党军事封锁,辗转抵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西井村分院,开展为期数月的医疗协助的经历。从她字数庞大的回忆录里,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解放区人民,在艰难的时境中尽可能地过得体面、幸福。
1947年底,盈露德(右)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西井村分院进行医护培训。
程方毅告诉南都记者:“从1887年盈亨利来到中国到1950年盈露德完成医疗援助工作离开中国。这个本是‘遥望者’的西方家庭在63年的光阴中亲历近代中国的变迁。回到美国工作、生活后,盈亨利的后人们一直精心地保存着他们与中国相关的所有资料。2019年初,他们通过我得知中山大学正在建设博物馆,决定将这批资料全数无偿捐赠,我们才得以有机会走近这个家庭以及他们记录的近代中国。”
独家专访——
程方毅:除了宏大叙事,还有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
从青铜器到家族档案的历史邂逅
南都: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研究盈亨利家族的近代档案?遇到过哪些挑战?
程方毅:契机源于2014年春季学期,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修读博士课程的我选修了一门名为“宾大博物馆的中国收藏”的课程,接触到一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我对这批青铜器的意涵和来源非常感兴趣。原来这批青铜器的来源与一位叫伊萨贝尔的女性有关——后来才知道她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师。通过博物馆档案,我联系到她的孙子肯尼斯·梅迩(Kenneth Mayer),2015年在弗吉尼亚州的老宅里,他母亲玛吉(Marjorie)突然搬出两箱东西,里面是大量的老照片、回忆录和通信记录,这些资料像拼图,逐渐拼出一个家族与中国63年的羁绊。
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是解读手写体,更难的是平衡学术性与故事性。我用了不少时间去交叉比对史料,以确保细节的准确性,让这本书既具有学术价值又能吸引普通读者。
南都:伊萨贝尔与“末代皇后”婉容的交往等是成书和策展时的重点内容,你是如何筛选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和细节的?
程方毅:其实也不用刻意筛选,将资料读一遍,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和细节会自动呈现。盈亨利家族故事有三位主角,分别是盈亨利、盈露德和伊萨贝尔,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的高光时刻,这自然也是故事性较强的时刻,大家也会比较感兴趣。在我看来,因为伊萨贝尔独特的“她者(others)”视角,让她留存的资料显得独特而珍贵。这里的“她者”视角由三个维度构成。首先是“旁观者”的维度。与另一位深度介入紫禁城局势的英文教习庄士敦不同的是,伊萨贝尔对在溥仪小朝廷中发生的事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让她较为冷静地记录并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第二个维度便是“女性”度。伊萨贝尔女性的身份能够让其进入婉容出嫁前的内闺和小朝廷的后宫,与比较“冷门”的内宫女性群体进行交流。并能敏感地察觉到很多其他资料少提及的细节,如宫廷内饰、帝后情绪、服饰等。第三个则是“外国人”的维度。有着异质文化背景的伊萨贝尔等人在与溥仪小朝廷打交道,并记录其经历时,都有其不一样的思考。她甚至成为婉容的倾吐对象,这一点从她留存的记录和日记可以看出。因此,她存留的资料能够与其他与溥仪相关的材料相互补充与印证,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小朝廷。
盈亨利家族故事多侧面展现了近代中外交流
南都:有没有特别珍贵的展品跟我们分享一下?
程方毅:在“禁宫内外”单元中有一子单元“皇后衣橱”,专门展出了伊萨贝尔与婉容、庄士敦于1924年6月11日在紫禁城内拍摄的一组照片、伊萨贝尔当天的日记以及她拍照时所穿着的婉容衣物(婉容后来把这件女袍赠予伊萨贝尔)。这组照片中既有单人照、也有两两组合的合照。在我看来,这组展品就很珍贵,它的证据链非常完整,既有文字记载,又有照片与衣物佐证,故事性非常强,所以我将这些材料单独罗列了出来。
1924年6月11日,婉容(左)与伊萨贝尔合影。
另外,我认为摄于1893年的盈亨利与中国助手并肩坐着合影的照片也非常珍贵。我们可以看到盈亨利在中国生活时与他合作的中国普通人的样貌——中国助手表情严肃,拿着折扇,一看就知道是接受过教育且自尊心很强的人。此外,盈露德珍藏的于1947年底摄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小鬼”照片也值得关注,可以看到“小鬼”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1893年,盈亨利与中国助手合影。
南都:研究盈亨利家族的在华经历,你认为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外关系等方面有着怎样的独特价值?
程方毅:作为近代西医东渐的先驱者,盈亨利曾担任通州潞河医院首任院长,并深度参与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筹建。其长女盈露德作为中国现代护理学科的奠基者,曾出任协和护理学院第二任院长。1945年至1950年间,她更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世界卫生组织特派专员身份重返中国。在通州潞河医院筹建初期,盈亨利即着手西医典籍的本土化译介工作。他口译美国医学教材,由助手管国全笔录整理,形成教学辅助材料以利学生研习。1909年,其译著《贺氏疗学》(Hare's Therapeutics)正式付梓;1914年10月,另一部译著《屈光学全卷》(Refraction and How to Refract)亦告完成。盈露德在开展医疗援助的过程中也编撰了不少培训教材。当讨论中外交流史时,我们不应忽略盈亨利父女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贡献。
1947年底,盈露德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西井村与同事们合影。
此外,伊萨贝尔在1922年至1924年间的日记中关于溥仪小朝廷的记载也值得关注。众所周知,1924年11月5日,溥仪、婉容等被人从紫禁城驱离,主流史料中婉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但是,我们在伊萨贝尔的日记中“听到”她的声音,这非常有趣。日记中记载了婉容大量的言论,在伊莎贝尔笔下,婉容是聪慧、优雅、美丽的小女生,并对新鲜事物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
所有这些史料不只是‘西方看中国’,更记录了两个文明如何彼此理解。展览想让观众看见,历史里除了宏大叙事,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
展讯——
“遥望与亲历:一个西方家庭眼中的近代中国”
时间:5月18日—12月31日
地点:中山大学博物馆专题展厅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何梦怡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发布于:广东省恒正网配资-泸州配资公司-配资平台排名前10名-配资杠杆炒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